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校学术著作培育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及其提升策略”(2015xzpy03);2015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促进研究”(2015cxsj072)。
作者简介:
甘婷婷,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014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吴翠萍,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the issues of employment quality concealed under the problems of employment quantity gradually become the concern of the public. Scholars have performed extensive studi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employment quality,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system, the related factors of employment and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employment qualit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summary, this study summarized and put forward that study on employment quality may present in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uture,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improving employment quality in China.
Key Words: Employment quality content index system factors development trends
引言
2004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动组织共同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就业论坛”,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对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了经济发展与就业相互促进的关系,认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就业结构的调整和特色的就业模式,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我国政府达成“促进就业质量,将充分就业和体面劳动作为劳动者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目标”的共识[1]。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就业乃是民生之本,并提出要推进全民更高质量的就业工作。那么,何为高质量就业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就业质量主要有哪些研究?本文对就业质量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同时对未来就业质量的发展趋势做了可能性的预测总结。
(一)就业质量的提出
国外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后期,在经历了美国的“工作生活质量”、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劳动”以及欧盟提出的“工作质量”之后逐渐被学者所关注[2]。尤其是国际劳工组织对“体面劳动”的解释研究,其中便涵盖了就业质量的内容。认为体面劳动是根据就业人员自身和其所属集体的条件,保障其自由、安全、尊严和公正的劳动,体面劳动的标准便是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权利与社会保障,在享有足够收入的同时让从业人员感到尊重[3]。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经历了社会经济萧条的重创,在失业人员众多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要提高从业人员“工作质量”的就业理念,并在工资,工作条件与内容,医疗保障等方面提出衡量工作质量高低的相关指标[4]。2007年,Schroeder Fredric K提出了“高质量就业”的定义,认为是个人对有着环境挑战和工作满意度的工作中所获得收入的能力,同时又指出除了收入之外应有其他的衡量指标[5]。该定义重点突出了个体对高质量工作的摄取能力。部分学者从就业质量的相关指标来定义就业质量,如:Kalleberg认为可用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来概括就业质量[6];Beatson认为就业质量是通过经济劳动关系契约和回报关系契约内容来衡量,偏重于经济学的定义[7]。
(二)就业质量的内涵
我国学界对就业质量内涵的界定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收入多少的综合概念[8];(2)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衡量包括就业机会、工作稳定性等各方满意程度的综合概念[9];(3)就业质量是一个递进的层次概念,从就业环境与人力资本的匹配程度到就业过程中的受保护程度以及抗风险的服务水平的逐渐递进的关系[10];(4)是个人或组织在就业过程中对就业事件的总判断,包括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11];(5)从就业中获取的全面的效用和价值[12]。
目前学界提出的就业质量定义相对具有代表性的是由李军峰、刘素华等提出的,将就业质量看成是对收入状况、工作条件、权利保障等满意度的多维的综合性的概念。诸多学者引用李军峰和刘素华的定义或由其定义引发的思考提出新的概念用于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当中。如:姚永告对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其以工作稳定为基础,以劳动报酬为核心,包括就业环境、职业声望、工作主观满意度在内的诸多方面[13]。米子川同样认为就业质量是一个全面性的概念,反映了劳动者对就业岗位的个人满足程度[14]。
二、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
在国外针对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典型研究有国际劳工组织对体面劳动的6个维度48个指标的操作、欧盟理事会对工作质量测量指标的10个维度的研究、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经济委员会对就业质量指数的公式计算以及欧洲统计协会对就业质量7个指标的评价。表 1是将以上研究单位提出的测量指标进行了归纳。
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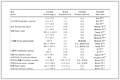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1 测量指标的典型研究
|
研究单位 | 指标分配 |
|
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4] |
工作机会;自由的条件下工作;生产性的工作;工作平等;工作安全;工作尊严(6个维度) |
|
欧盟理事会:工作质量测量[4] |
内在工作质量;技能、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性别平等;健康和工作安全;灵活性和安全性;包容性和劳动力市场进入;工作组织和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对话和员工参与;多样性;非歧视(10个维度) | |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经济委员会:就业质量指数[4] |
就业补偿指数;就业稳定性指数;全职就业比重[0.5×(就业补偿指数+就业稳定性指数)×全职就业比重] | |
欧洲统计协会:就业质量指标评价[15] |
职业道德与安全;工资与福利;工作时间及工作与生活的协调;就业保障及社会保护;社会对话;技能发展与培训;职场人际关系与工作动机(7个指标) |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
|
表 1 测量指标的典型研究
|
根据国外学者对就业质量指标的界定,国内学者也逐渐关注就业质量的测量指标,表 2是将我国几位代表性学者所提出的测量指标进行了归纳。
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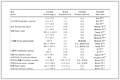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2 我国代表性学者提出的测量指标
|
学者,年份 | 指标 |
|
刘素华,2005[8] | 工作的性质;聘用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 | |
李军峰,2003[9] | 就业稳定性指数;工作质量指数;劳资关系指数;福利和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 | |
何亦名、王翠先、黄秋萍,2012[16] | 工资福利水平;就业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就业渠道;劳动合同期限;劳动时间;在职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关系;居住情况 | |
柯羽,2010[17] | 就业满意度;职业发展前景;人职匹配度;薪金水平;就业单位性质和就业地区流向 | |
马庆发,2004[18] | 职业声望;职业期望满足程度;职业成就;职业锚;专业方向与职业的适应性;人职匹配 | |
张桂宁,2007[19] | 平等和权利保护;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报酬、工作条件;健康与安全;福利和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前景 |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
|
表 2 我国代表性学者提出的测量指标
|
2011年11月5日,《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该报告是中国第一个将劳动力的关注点投放在就业质量的问题上,报告除了设定就业质量指数包括就业环境、就业能力等在内的六个维度之外,还设定了就业质量的二十个二级指标和五十个三级指标,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赖德胜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就业质量不高,其表现在:首先,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包括就业歧视和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其次,劳动者收入差距大,工资增幅慢;第三,社会保障的力度小,保障水平不高;第四,劳资关系存在问题等,就业质量问题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
三、影响就业质量提升的相关因素研究与对策建议
我国学者对就业质量提高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国内外学者对就业质量的内涵与指标研究的学习启发下开展对特定群体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实证研究居多。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就业质量仍然较低,影响就业质量提高的因素较多且各因素之间交织复杂,以农民工为例,主要存在宏观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就业环境,制度和政策三个方面,以及微观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收入,劳动权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1. 宏观影响因素
(1) 区域经济。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工人的工资、福利等水平都偏低,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大量外流,尤其对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意愿十分强烈,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高质量的就业、社会福利的完善成为他们考虑流动的首要因素[21]。朱火云、丁煜、王翻羽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就业质量指数调研分析得出经济发展的高低和就业质量高低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同时指出,经济发展并不是决定就业质量高低的唯一因素[22]。
(2) 就业环境。黄闯从金融危机引发的民工荒视角出发,指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如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失去了生活保障。从某种程度上看,民工荒的出现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的选择,然而其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层次不高、就业市场壁垒与巨大的市场竞争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的大环境并没有改变。若想提高就业质量,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明确自身短板,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实现高水平就业的质变目标[23]。潘琰、毛腾飞明确提出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就业环境的不同会对就业者的生活成本和未来工作发展造成就业质量上面的差异[24]。
(3) 制度和政策。城乡二元体制长期以来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以及由城乡二元制度带来的户籍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有着巨大的差别,尤其体现在就业的差别待遇上,包括福利待遇、工资收入、职业发展等等。尽管我国《劳动合同法》宏观上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但在实际运作中操作性弱,法律的实效性跟不上现实情况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及时得到维护,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难以得到提高[25]。王阳根据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构建与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指数得出制度和政策调整对就业质量有延迟性影响的结论。认为我国当前就业的相关体制与政策较为不完善,如社会保障与保险覆盖面不高,就业市场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健全,劳动力培训力度较小,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等,制度与政策是就业质量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10]。
2. 微观影响因素
(1) 工资收入。工作首要的回报便是工作带来的收入报酬,与城市职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从事的是低端产业 ,技能水平要求不高,职业的稳定性较差,企业对其人力资本不看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偏低。同样,收入与职业的稳定性相互作用,经济理性使农民工产生职业观望态度,寻求机会跳槽,在增加了风险资本之余降低了就业的稳定性,影响了就业质量的提高[26]。谢勇通过工资方程和计量模型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获得的包括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和人力资本等较高的就业质量便容易提高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会提高农民工工作匹配质量[27]。从效率工资理论出发,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进而促进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减少偷懒行为,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了企业整体的运作效率,尤其是对东部地区部分“低收入-低素质、低技能-低收入”的低就业质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上调农民工最低工资水平容易让农民工走出就业困境,实现高质量就业的目标[28]。
(2) 劳动权益。在过去,“农民工”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和差别待遇。现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生活观念、职业选择、就业能力等多方面与老一辈农民工比较都有着较大的改善和提高,然而诸多用人单位仍然以固有的刻板印象衡量他们,在岗位选择和工资待遇上差别对待,极大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就业过程中的积极性,影响了其就业质量的提高[29]。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主要受到包括用工地区就业保护主义下的就业不平等、较少地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无保障、休息休假权益难争取、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差等几个方面的侵犯,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职业发展[30]。
(3)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彭国胜通过对长沙市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研得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的结论。人力资本方面的年龄、性别、户籍地、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对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收入和职业发展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除了受到自身人力资本的影响外,还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尤其是群体异特质中的弱关系施加影响[31]。钱芳、陈东有重点地针对社会资本的强-弱关系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社会资本的存有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可获得信息的多少以及就业的可选择范围的大小,而大多数农民工所属亲缘、地缘强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资源狭窄、工作类型结构单一、人际交往圈小的强关系社会网络无法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产生积极作用[32]。
1. 宏观对策
(1) 完善劳动力市场,宽松就业环境。从就业环境来看,创造较为公平的就业环境,有助于改善就业不稳定、劳资问题突出、劳动者就业权益难保障、劳动者工资报酬过低的现象,宽松就业环境,实现劳动者灵活就业[10]。陈吉胜从人才资源市场出发,认为提高就业质量必须构建统一的就业市场,提高人力资源市场的服务水平,加大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33]。高兴艺指出建立地区间平等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前提[34]。
(2) 完善制度,政策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就业作为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作用,明确就业政策,推动高质量就业的实现[35]。从制度体系改革出发,大力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与保险体系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体系。企业要规范用人制度,明确就业职责,加强就业者的职业教育工作,对促进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高有重要意义[36]。从货币政策对就业质量影响方面来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有助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37]。
2. 微观建议
(1) 增强就业能力,加强技能培训。强化技能培训,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体现素质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的重要作用[38]。2012年河南省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工作,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尽早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和社会融合[39]。
(2) 增强就业资本,拓宽就业渠道。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机会、职业选择和职业适应的影响显著,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就要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由生存型择业到发展型择业的转变[40]。从人力资本的作用来看,就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就业能力的表现,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人更容易从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高质量的工作。因此,加强人力资本的建设对实现高质量就业有积极作用[41]。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结合作用来看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状况、技能水平等方面)强的就业者更具有就业优势,同时社会资本(直系亲属状况、家乡来源、获取工作的途径等方面)强的就业者也有助于增强其工作的稳定性[42]。
(一)研究结论
首先,在就业质量的概念定义中,需明确以下三个范畴。第一,就业质量概念既关乎国家层面,又与个人层面有关。就业质量低下不利于劳动者潜力的开发,除了对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职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外,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强调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性,可见就业质量已成为我国城镇化战略中的关键问题。第二,就业质量应该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相结合的概念。宏观上包括当前经济发展的背景、劳动力市场、工作性质等方面,微观方面表现为对农民工、毕业生、女性等特定群体的就业质量研究。第三,就业质量指标评定标准既有客观评定又有主观评定。客观上包括对就业地区、就业单位、就业保障、收入报酬等指标的评价研究,主观方面如对就业满意度、职业发展等研究。
其次,在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方面,可以看到不同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设定将就业质量进行了不同维度和指标上的操作化,包括就业市场、工作性质、工作环境、人职匹配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多层次的评价体系,通过指标构建的实证研究,不难发现我国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尤其是农民工、女性等弱势群体在就业过程中容易遭受不平等待遇,除了就业市场的壁垒,还存在个人对工作的不了解以及淡薄的权利维护意识,无法在就业过程中发挥自身能力,实现职业的高层次发展。
再次,在对特定群体进行研究时,要根据群体间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特点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如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研究,要首先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三高一低” 的特点,即教育水平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收入报酬低的特点(石丹淅、赖德胜、李宏兵,2014)。这就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和技能的接受程度比老一辈农民工要高,企业可有针对性地对入职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一些职业培训,有助于选拔优质人才。
(二)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对就业质量的文献阅读,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就业质量的相关研究做了很多细致深入的工作。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集中于对就业质量的内涵研究和就业质量的指标探究以及基于就业指标微观视角的特定群体的实证研究。从就业质量的概念来看,基于国外体面劳动和工作质量等有关“就业”“质量”的定义,围绕国内相对权威的就业质量定义展开概念界定。从就业质量评价指标选取上看,不同学者有不同维度上的划分,大致包括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以及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类,对特定群体的实证研究较多,如: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女性职工就业质量研究,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等。
由于“就业质量”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国内针对就业质量研究空间较大,创新性强。未来关于就业质量研究可能呈以下几方面的趋势:第一,就业质量的维度指标选取更加全面完整,研究视角综合性更强,考虑的就业质量指数更加客观准确。第二,就业质量的研究建立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逻辑更为严谨。有关就业质量的特征问题研究、对策研究等都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多地从理论转向现实研究。第三,定量的数据研究,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和权威。在定量的大数据时代,研究要讲究科学性、准确性和权威性,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在数据的使用上引用官方数据多,数据的获得和分析都严格按照科学的统计抽样和统计分析来进行。第四,讲究研究对象的具体性,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将研究问题聚焦到特定群体就业质量上,设计的维度、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就业质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研究课题,提高就业质量不仅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更是实现个体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因此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宏观层面的努力,微观层面也要积极面对,只有全社会集思广益,未来的就业质量才能稳健上升。
 2016
2016 Issue (3): 80-85
Issue (3): 80-85 2016
2016 Issue (3): 80-85
Issue (3): 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