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6-03-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5SJD099);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资金资助(PPZY2015A059);南京农业大学院级教改项目资金资助(2016YJ04T)
作者简介:
朱冰莹,女,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农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管理; 董维春,男,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引言:从世界一流大学到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的相继提出,以及“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的开展,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已成为高教界的热点。1999年,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科院西北植物所、中科院水土保护所、陕西农科院和陕西林科院等机构合并重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发展目标。2002年,中国农业大学瞿振元和陈章良向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汇报工作时提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目标,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2009年5月2日,胡锦涛视察时提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要求。2011年,南京农业大学提出“1235发展战略”,明确了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设目标。
但国内外学界对有无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尚存在争议,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定论不一。本文综合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QS世界大学排名(农林学科)①、台湾大学世界大学论文质量排名(NT-农业领域)以及ESI学科排名②等指标,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探究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设路径。
一、澄清争论:有无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基于国外名称带“农”高校的日趋减少,首先对“有无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及“什么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进行解析。
(一)基于大学校名的直观理解
基于校名的直观理解,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即“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进而产生如下问题:是否仅以世界上称“农业大学”的机构为样本来评价“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自19世纪以来,各国农业大学历经独立、兴衰和重构,特别是二战后的工业化浪潮使名称上叫“农业大学”的高教机构锐减。各类世界大学排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校名的演化,如:ARWU排行中,进入500强的151所美国大学中,赠地学院(均产生于1862年)56所,占近40%。这些机构名称几经变迁,到2007年,带“农”的已降至15%,没有“农”的占近50%(见表 1)。ARWU全球 500强大学中,带“农”字的仅有德克萨斯农工大学(100位)、瑞典农业科学大学(301~400位)和中国农业大学(301~400位)。
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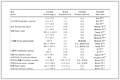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1 美国赠地学院农学院名称演变
| (%) |
|
学院名称 |
年份 |
|
1962 | 1974 | 1988 | 1993 | 2007 |
|
农业(Agriculture) a | 86 | 64 | 58 | 45 | 15 | |
与家庭经济(and Home Economics) | 14 | 8 | 8 | 7 | 1 | |
与自然资源(and Natural Resources) | | 6 | 8 | 13 | 15 | |
与生命科学(and Life Sciences) | | 14 | 14 | 15 | 13 | |
与环境(and Environment) | | 4 | 2 | 4 | 4 | |
院名中没有“农业” | | 2 | 6 | 9 | 49 | |
其他b | | 2 | 4 | 7 | 3 |
| a: 包括农业 (Agriculture) 和农业科学 (Agriculture Sciences);b: 农业与生物科学 (Agriculture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
|
表 1 美国赠地学院农学院名称演变
|
(二)基于知识生产的理性判断
作为多学科的集合体,对大学的认识不应仅拘泥于校名的直观理解,而应基于大学和学科的重要基础——知识生产。如图 1、图 2所示,NTU、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的涉农大学,主体分布于ARWU前300区间中。且ARWU Top100大学中约60%具有一流农业学科。可见,“一流农业大学”理所应当是“一流大学”,两者只是概念的外延有所差异,在内涵上并无本质区别[1]。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一流农业大学重要特征是拥有若干世界一流的农业及相关学科,且这些学科及学科领域拥有极大世界声誉和排名在世界前列。
(三)基于模式演化的特征分析
从大学模式演化来看,18世纪后期的德国大学(如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群的崛起(如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标志着认识论哲学指导下从事顶尖基础研究和精英人才培养的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二战后,基于政治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在联邦政府出台的《贝耶·多尔法案》(Bayh-Dole Act)推动下,以硅谷现象、大学科技园的出现和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在产学研三螺旋制度框架下形成了创业型大学。此外,起始于林肯时期的《莫里尔法案》(Morill Act)通过将农学院、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推广体系结合,将农业学科嵌入传统大学并形成了世界一流农业大学[2],其交叉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 3所示。同时具备三类大学特征的是那些农业及农业相关学科优势明显的世界一流大学。如表 2所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首先表现为研究型大学的共性特征,包括雄厚的办学经费、一流师资队伍、精英人才培养、原创性科研成果和突出的社会服务等核心竞争要素。其次表现为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包括先进的教育理念、优秀的大学文化及进取型学校管理。另外,还具备农业与生命科学特色突出等特征及公益性组织行为方式显著等个性特征。
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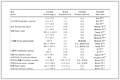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2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十项特征
|
分类 | 特征 | 具体要求或行为方式 | 竞争力
|
| 研究型大学 |
雄厚的办学经费 | 大学、政府、市场协调三角形 |
国际知名度
学术竞争力
社会影响力
产业依存度
文化软实力
校友归属感 |
|
一流的师资队伍 | 国际化的学者与学术团队 |
|
精英人才的培养 | 生源质量、教育模式 |
|
原创性科研成果 | 学术大师、科学前沿 |
|
突出的社会贡献 | 一流的科研为基础 |
| 学科特色 |
农科与生科特色 | 农学、食品、生物、环境等 |
| 一流大学 |
先进的教育理念 | 人与社会的双重完善 |
|
优秀的大学文化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
进取型学校管理 | 战略引领性、治理现代性 |
| 校友社区 |
大批的杰出校友 | 大学输向社会的忠诚使者 |
|
表 2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十项特征
|
二、比较借鉴:世界顶尖农科大学的轨迹演化
比较世界顶尖涉农大学(见表 3)的模式演化和发展路径,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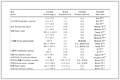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3 几大排行榜上的世界涉农大学
|
大学名称 | ARWU 2013 | Times 2013 | QS-2013 农林 | QS-2014 农林 | NTU-Ranking 2012农学 | NTU-Ranking 2013农学 |
|
康奈尔大学 | 13 | 19 | 3 | 3 | 3 | 3 | |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 19 | 30 | 4 | 4 | 7 | 6 |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 47 | 52 | 1 | 1 | 1 | 2 | |
瓦赫宁根大学 | 101~150 | 77 | 2 | 2 | 2 | 1 | |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 101~150 | 159 | 5 | 9 | 31 | 33 | |
昆士兰大学 | 85 | 63 | 7 | 18 | 12 | 12 | |
墨尔本大学 | 54 | 34 | 42 | 36 | 41 | 46 | |
雷丁大学 | 301~400 | 194 | 11 | 11 | 101 | | |
东京大学 | 21 | 23 | 19 | 13 | 19 | 25 | |
京都大学 | 26 | 52 | 17 | 25 | 38 | 45 |
|
表 3 几大排行榜上的世界涉农大学
|
(一)美国模式:赠地大学群体性崛起
作为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基石和里程碑[3]及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典范,美国赠地学院(Land Grant College) 的群体性崛起是美国联邦政府政策推动和大学自觉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策层面看,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的《莫里尔法案》(Morill Act)推动了农学院体系的建立;在1887年《哈奇法案》(Hatch Act)资助下,创建了地方农业试验站体系;在1914 年《史密斯—利弗法案》( Smith-Lever Act)支持下,形成了合作农业推广体系。在三位一体的联邦法案的作用下,到1900年,标准的农业学科体系建成③,农学院中形成了完整的系、试验站、推广站、示范农场等组织架构。
在大学层面,以促进大学文雅教育和实际研究紧密结合、适应社会和个人双重发展需要为核心的“康奈尔计划”(Comell Plan)[4],和主张大学与州政府紧密合作、大力发展知识的推广和应用的“威斯康辛思想”的形成,推动了大学世俗化和社会服务职能形成,使赠地学院在美国农业产量持续提升和农业科技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1876年,康奈尔大学授予全美第一个DVM学位,成为职业学位的典范。1904年,在范·海斯(Van Hise)校长推动下,威斯康辛大学通过维生素专利推广奶牛计划,使威斯康辛州从农业不发达州发展成农业发达州。
(二)荷兰模式:瓦赫宁根大学独树一帜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花卉、奶酪出口国和第三大农牧产品出口国的荷兰,其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由5所农学院和瓦赫宁根大学构成[6]。作为荷兰唯一的多学科综合性农业大学和世界顶尖农科大学,瓦赫宁根大学(WURC)是综合性大学和国家农科院的复合体。它起源于1873年荷兰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农业学校和试验基地,之后几经更名,从1876年的瓦特宁根市农业学院到1904年的州立农业园艺与林业学校,再到1918年的瓦特宁根学院,1986年更名为瓦特宁根农业大学,1997年与荷兰农业科学院合并,成立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 Center,WURC)。2003年劳伦斯坦农学院并入万豪劳伦斯坦大学,2004年该校并入瓦赫宁根大学。经历百年的积累和多次合并,可以说,WURC凭借资源、学科和人才等的集聚优势,成为世界顶尖的农科大学。
(三)法国模式:农业专科学校与农科院日趋结合
作为欧洲第一农业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法国农业教育历史悠久。早在1848年,法国国民议会就批准在图鲁兹建立法国历史上第一所农业技术学校。1960年以后,法国调整和优化农业教育,完善农业教育体系(形成2年制的高等技术教育、4~5年的工程师教育和6或8年的研究生教育),确立农业教育的先导地位[7],促使农业专科院校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最早(1946年)成立国家农科院的国家,法国的农业大学和农业科学研究院向着密切配合的方向发展,如雷恩农业大学和雷恩农业研究中心结合成为雷恩农业教育与科研复合体、国立阿尔福兽医大学和兽医研究院结合成一体等[8],由此形成的资源共享机制和优势互补效应奠定了法国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重要基础。
(四)澳大利亚模式:综合性大学农学院重点突破
经历百年历史和近40年快速发展,澳大利亚形成了由综合性大学、高等教育学院及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构成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主要从事高级农业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大学农学院,侧重基础理论研究和科研训练。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农业生物学领域对固氧机制、细胞分裂控制、植物再生等问题进行攻关;作为全国唯一可授予各类农业工程学位的墨尔本大学,在农业工程学领域研究灌溉最佳数学模型、无线电遥控、饲料加工等问题;研究生占在校生57%的阿得莱德大学,其维特农业研究院则专门培养高级研究人员[9]。综合性大学农学院的整体前行,使其在2010年世界大学科研论文榜亚太地区农学前10名中占据六席,形成了诸多综合性大学以从事高水平农业及与农业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趋向。
(五)日本模式:综合性大学农学部聚集优势
作为日本农业教育的两翼,隶属文部省系统的学校农业教育和隶属农林水产省以及各县的农业继续教育构成了日本高等农业教育体系[10]。高等农业教育除在少数几所农业大学(如国立的带广畜产大学、东京农工大学,公立的东京水产大学,私立的东京农业大学等7所农业大学)开展外,主要在综合性大学的农学部实施。这些农学部亦可分为两类,一类由独立农学院转入综合性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农学部,如北海道大学、神户大学及东京大学等大学的农学部。以东京大学为例,1940年代末,东京大学设法学部、医学部、农学部等9个学部。另一类是综合性大学内重设农学部,如东北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大学的农学部。以京都大学为例,其农学部成立于1923年,包括应用生命科学、农业环境工程、食品与环境经济等10个系53个讲座,以及农场、林场、牧场等研究设施,并于1953年成立了包括若干分部的农业研究生院。以上两种模式均反映出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科研综合优势对日本形成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支撑作用。
总之,考察世界顶尖农业大学的演化,可以发现:①世界一流农业教育大多存在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②农学院及与农业学科已远超过成立时的范围,向着交叉性、综合性方向发展(如表 4所示),各校ESI学科综合指数和农生环覆盖率均达到较高水平④;③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实施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运行机制。
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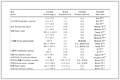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4 世界农科四杰学科概况
|
学校 | 学院结构 | ESI学科数 | ESI学科综合指数 | 农生环覆盖率
|
|
康奈尔大学 | 农业与生命科学、兽医、人类与生态、工业和劳资关系、建筑规划和设计、文理、工程、酒店管理、医学、法学、管理 | 22 | 100% | 9/9 | |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 农业与生命科学、商学、教育、工程、人类生态、环境、法学、文理、医学、护理、药学、兽医 | 22 | 100% | 9/9 |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 农业与环境科学、工学、文理、生物、管理、教育、法学、医学、兽医 | 21 | 95% | 9/9 | |
瓦赫宁根大学 | 五个学部:植物科学,动物科学,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 | 13 | 59% | 8/9 |
|
表 4 世界农科四杰学科概况
|
三、实然考察:成效与差距并存的中国涉农大学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既要有公认的学术标准,又要体现中国国情和学校特色。笔者将从成效与差距两个维度对中国涉农大学进行现实考察。
(一)层次界分:中国涉农大学的综合进程
核心指标指基于论文反映世界一流农业大学高水平、高质量和高影响力的计量指标。综合我国涉农大学在QS、NTU和ESI学科中的表现以及黄金分割原则,将中国涉农大学的发展进程界分为三个层次,其具体界分标准如表 5所示。
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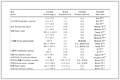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5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界分标准
|
层次/标准 | 大学指标 | 学科指标 |
|
第一层次:顶尖涉农大学 | QS和NTU前20 | 进入ESI前1‰学科≥1 |
|
第二层次:一流涉农大学 | QS和NTU前100 | 进入ESI前1%学科≥5 | |
第三层次:高水平涉农大学 | QS和NTU前300 | 进入ESI前1%学科≥1 |
|
表 5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界分标准
|
依据上述评价指标对我国部属农业高校进行考察,结果如表 6所示。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涉农高校还未进入世界顶尖农业大学行列。其次,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在QS-2014农林和NTU-2013农学分别位于51~100、38位和43、42位,9个农业学科及农业相关学科全部进入ESI前1%,可以说已基本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稳步发展,不仅在QS-2014农林和NTU-2013农学处于前200位(除西北农林在NTU位于201位),且均有两个及以上的农业学科及与农业相关学科进入ESI前1%,步入高水平大学行列。
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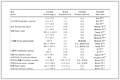
表 6 中国涉农大学界分情况
|
层次/标准 | 大学名称 |
大学排名 | 进入ESI前1%
| |
QS-2014农林 | NTU-2013农学 |
|
第一层次:顶尖涉农大学 | | | | |
|
第二层次:一流涉农大学 |
浙江大学 | 51~100 | 38 | 9个 | |
|
中国农业大学 | 43 | 42 | 9个 |
|
第三层次:高水平涉农大学 |
南京农业大学 | 113 | 109 | 4个 | |
|
华中农业大学 | 162 | 138 | 2个 | |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170 | 201 | 2个 |
| (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QS世界大学农林学科前200名、2013年台湾大学榜世界大学科研领域论文质量Top300和2013年ESI学科排名统计而得) |
|
表 6 中国涉农大学界分情况
|
农业学科在ESI前1%学科排名前100位中,中国大学占据三席,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32位)、浙江大学(51位)和南京农业大学(100位);前100~200位中,中国大学仍有三席,分别是江南大学(130位)、华中农业大学(133位)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4位)。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农业学科同样表现出强劲实力,华南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扬州大学等均进入农业科学ESI前1%。这些数据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涉农大学赶超世界顶尖高水平大学的强劲势头,另一方面进一步澄清了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内涵,即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界定,不应拘泥于校名的直观理解,而应着眼传统农业科学及与农业相关科学领域的卓越发展。
(二)潜能分析:中国涉农大学的学科走势
在综合进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涉农大学学科发展潜能。中国农业大学9个涉农学科均进入ESI前1%,所以此处仅对南京农业大学6个学科,华中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7个学
科作潜力(SCI检索限制时段不能控制到月份,与ESI相比,数据量略多,潜力值偏乐观)对比分析(潜力=学科近10年总被引频次÷学科全球前1%被引频次域值×100%;大于50%为潜力学科),如图 4所示。
南京农业大学6个未进入ESI前1%的涉农学科中,潜力学科有4个,分别为生物与生化、微生物、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和工程学。表明了生物与生化(107.6%)、微生物(89.14%)有望快速成为该校新的ESI学科。华中农业大学7个未进入ESI前1%的涉农学科中,潜力学科有6个,分别为生态与环境、生物与生化、微生物、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工程学和化学。生物与生化(99.95%)、化学(88.45%)有望快速成为该校新的ESI学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7个未进入ESI的涉农学科中,潜力学科有4个,分别为生态与环境、生物与生化、工程和化学。其中生态与环境(92.45%)、化学(88.45%)有望快速成为该校新的ESI学科。可以说,中国涉农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方面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学科和科研基础。
(三)差距判定:中国涉农大学的目标指向
明确与世界顶尖农科大学的差距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前提。将美国农科大学的杰出代表(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和中国两所部属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进行比较,论文发表趋势对比结果如图 5所示。1981~2011年的30年间,美国两校论文数量持续提升,均从2500篇左右增长至5500篇左右,而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论文增长的转折点则出现在2000年前后,仅获得了10年的发展,这也是两国涉农高校知识生产能力存在着“巨人与侏儒”般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2011年,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的论文数相当于中国农业大学的3.6倍和南京农业大学的7.8倍。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世纪之交的中国涉农大学正加速崛起,2000至2010年间,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论文增长速度明显提升,两校2000年各自的论文总量均在1000篇左右,到2010年各自已达2500篇,若消除文献的语言障碍,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的差距,由50年降至30年(相当于美国两所高校1980年的水平)。
(一)持续提升农业学科及学科群实力,保持竞争优势
学科是大学办学思想、制度的直接承担者和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学科建设是学校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基本建设,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国外顶尖大学发展模式证明,农业学科群的卓越发展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形成的基础。要建成世界一流农业大学,首先要建设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世界一流农业学科及学科群,这也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涉农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学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要实现“一流”,首先,就单个学科而言,应依据科学逻辑和社会急需不断凝练学科方向。其次,在学科及学科群之间,应发挥学科结构优化的协同效应,使农科、理科生物学、工科及经济管理等传统涉农学科优势互补,实现传统涉农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第三,在学科综合发展战略上,应坚持继承优势与拓展领域的统一,坚持科学性、前瞻性、创新性的统一。科学定位,发挥学科优势和特色应当成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选择。
(二)突破知识瓶颈,优化学科结构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中等水平的陷阱”。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云:“涉浅水则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对于大学的学科结构而言,适应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突出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等主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的同时,彰显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的重要支撑作用是学科结构优化的前提。因为强化发现问题深度,形成新思想的哲学,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元知识的数理,是突破单科性学校的知识瓶颈的关键。国际经验证明,世界顶尖涉农大学都具有优秀的文理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学科结构。因而,形成以农业哲学、乡村文化、新农村建设、新闻与传媒等为主的人文科学体系,由应用数学、资源与环境等组成的基础科学体系,以及由信息科技、农业工程、食品科技、建筑设计等构成的技术和工程科学体系及其交叉融合,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必由之路。
(三)推动协同创新,彰显公益性组织行为
美国增地学院的发展历史表明,彰显公益性组织行为是世界一流大学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在小科学时代向大科学时代迈进过程中,推动协同创新机制,建立由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多主体组成的协同创新中心,是中国涉农大学提升科研水平和服务力度的重要选择。就各创新主体而言,通过不断吸取、整合、开发和优化各种资源,包括人才、知识、信息、资金、设备、制度及文化等多个创新要素,是协同创新机制形成的基础,因而培育“跨越边界,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是各创新主体跨边界合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政策层面而言,政府应着力强化指引作用,通过政策法规的引导,推进柔性无边界或跨边界组织的创建,构建良好的协调机制,发挥各方在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优势和作用。目前,江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建立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作物基因资源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总之,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和区域经济的战略性合作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路径选择。
[注释]
① QS世界大学排名是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包括主要的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和学科排名。另外,QS还推出了独立的地区性排名,如《QS亚洲大学排名》。本文主要引用其2013和2014年推出的世界大学农业学科排名。
②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是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2001年推出的,基于SCI(E)和SSCI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期刊,利用Web of Science 10年滚动数据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分成22个学科;学科排名根据机构的学科被引频次从多到少排序,只有进入前1%的才给出机构学科排名,一个机构最多有22个学科和1个学科整体排名。
③ 这一时期的农业科学体系主要包括土壤学、农学、植物病理学、园艺学、畜牧学、兽医学及农业经济学等。
④ ESI学科综合指数=ESI学科数÷22×100%,反映大学一流学科的综合性;农生环覆盖率=对9个涉及农业、生物、环境类的特色学科的拥有程度。
 2016
2016 Issue (2): 16-23,36
Issue (2): 16-23,36 2016
2016 Issue (2): 16-23,36
Issue (2): 16-2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