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陈建伟.
- Chen Jianwei.
- 教育的婚姻回报:“学得好”与“嫁得好”
- The Return of Education from Marriage Market: Better Education and Better Marriage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7(6): 22-34,100
-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5, 17(6): 22-34,100.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5-10-11
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Hannum和Xie,1994)。这与Barro 和 Lee(2013)全球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女性教育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相对南亚国家女性受教育相对不足的状况①,中国在提高女性教育水平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普通学校在校生中女学生所占比例持续上升(目前普遍超过了45%),2006年以后女性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超过了男性(卫倩平,2010)。各级教育女性入学率的普遍提升,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女性教育成就显著,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上一代人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叶华和吴晓刚,2011),城乡间的趋势同样如此(张兆曙和陈奇,2013)。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改善幅度高于男性,而且在男性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中女性受教育水平相对更高。
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地区办公室对南亚国家女性受教育的研究发现,提高南亚国家女性教育水平还存在较多障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参见Unicef(2009),Overcoming Barriers to Girls’ Education in South Asia.
如何解释我国近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相对提升,尤其是在“男性偏好”的不利条件下,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改善的现象呢?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女性受教育水平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非常关键。一种解释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逻辑结果。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生育的子女数量下降,并且影响了子女的性别构成,有效地降低了兄弟姐妹数量对女性教育获得的非对称性影响,从而推动男女教育的平等化发展(叶华和吴晓刚,2011),Lee(2012)的研究也认为女性教育水平的相对提高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意外结果。家庭经济学研究认为,父母可能在生育和教育投资方面存在性别偏好(BenPorath和Welch,1976),由此导致具有多个子女的家庭中女孩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教育成就也低于男性。Butcher 和Case(1994)基于美国经验同样发现,那些只有兄弟的女性比具有姐妹的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从家庭经济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对提高女性教育成就有重要作用。也有研究认为地区经济社会的普遍均衡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提高女性教育水平,缩小性别差异(牛建林和齐亚强,2010)。还有研究认为,家庭经济条件虽然显著影响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但不存在性别差异,虽然男孩上大学的机会相对女孩更多,但是高等教育扩招之后男性的优势在下降,而农村地区下降的幅度更大,从而使得农村地区女性得到了更多新增教育机会,改善了其教育劣势地位(张兆曙和陈奇,2013)。另外,基于澳门的经验研究认为,政府推广和普及义务教育,直接增加了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柯丽香等,2013)。
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教育的经济回报和制度变革等方面的因素,来解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理论上,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取决于个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努力程度、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政府和社会教育资源的供给。从我们掌握的政策文献来看,并未发现性别歧视的公共教育政策。而且,系统性文献回顾也没有发现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显著较大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差异(Buchmann等,2008)。因此,要理解性别不平等的缩小,需要追踪个人和家庭教育资源的投入激励机制,以探明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女孩相对男孩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本文将从教育的婚姻回报来分析家庭和受教育者面临的教育动机,并认为特定条件下女性接受教育的激励相对上升,最终转换为女性教育成就的快速提高。婚姻市场存在依配偶教育特征的正向分层配对,夫妻双方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正相关,也可以称之为教育同质匹配。教育的婚姻回报率为正,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匹配到受过良好教育对象的概率也越高。可以合理地假定,配偶的教育水平越高,婚姻配对的效用也越高,对于婚姻市场的潜在进入者而言,尽可能地匹配到高教育水平的配偶符合婚姻效用最大化原理。婚姻市场未婚男性增加引起性别比率失衡,而男性相对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女性比较稀缺,因此女性受教育能够获得更高的婚姻回报率。为了匹配更高教育水平的对象以提高未来婚姻效用,可行的办法是进行更多的婚前教育投资,把自己变得更具有吸引力。这样一来,女性相对男性具有更强的教育投资激励,为了实现“嫁得好”(嫁一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丈夫)而努力“学得好”(达到更高教育水平)。这有助于解释近年来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相对快速提升的事实。对于农村女性而言,虽然教育的婚姻回报率不及城镇女性,但高于农村男性,因此农村女性也具有充分的激励接受更多的教育。农村男性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来自婚姻的激励程度在下降,因此农村男性接受更多教育的动力相对较弱,这值得我们警惕。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分析教育的婚配激励,并提出待验证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并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与估计方法;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的分析与讨论;最后是本文的小结。
二、教育的婚姻回报与女性的教育投资激励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因为教育能够带来正收益。这种收益既可能是未来更高的收入,如经验估算文献表明,各级教育投资存在显著正的回报率(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2004);也可能是未来更好的婚姻与家庭生活。教育的经济效应已经得到太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注,而对教育的非货币效应的研究正处于一个令人兴奋的阶段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Oreopoulos 和Salvanes,2011),教育的婚姻效应便是其中的重要分支。由Becker(1973)构建的婚姻经济学分析框架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其一,每个人都尝试寻找一个最佳配偶来实现福利最大化,这一福利可以由婚姻后的家庭生产的产品来衡量,福利效用可在婚姻双方之间转移;其二,婚姻市场的均衡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没有人能够从改变配偶的行动中获得福利改进。在此基础上,婚姻双方的有形财产、教育、智力、外貌特征、民族身份等特征,可以很好地在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这一分析框架自提出以来沿用至今,Eugene和Aloysius(2006)在这一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婚姻匹配函数,分析了性别比率变化的影响,以及年轻一代在婚姻中的福利收益与福利损失。
教育的婚姻回报,我们定义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对匹配到良好教育水平对象的作用①,婚姻市场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未婚者能够匹配到更优秀的婚配对象。如果个人教育有助于匹配到受过更好教育的对象,那么可以认为教育的婚姻回报为正。一般稳定状态下,婚姻市场更多的是同质性匹配模式(Kalmijn,1998),婚配双方的教育水平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教育的婚姻回报显著为正。为什么有如此结果?Mare(1991)认为教育同质匹配部分取决于偏好,部分取决于毕业离校后进入婚姻所经历的时间长短。当然,婚姻市场同等教育水平婚配对象的可搜寻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McPherson等人( 2001)认为,人存在着同质性偏好,相似性产生了相互联系进而形成社会网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美国的经验表明,1960年以来美国人婚姻的教育分层趋势不断强化,念过大学的人更可能与同等学力的人结婚(Schwartz和Mare,2005)。然而,在婚姻效用不可转移和个体异质性等条件约束下,婚姻市场也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和非同质性匹配,婚姻市场搜寻的结果可能出现向上匹配(Burdett和Coles,1997)。尤其是在性别比率失衡的状态下,处于性别优势的一方更倾向于也更容易选择“向上婚配”(marrying up)(Abramitzky等,2011)。不管是同质性匹配还是向上匹配,受过良好教育的对象总是会得到更多青睐而处于比较优势地位。正因为更多地投资婚前教育有助于把自己在婚姻市场上变得更具有吸引力(Lafortune,2013),个人才有充分的动力为了匹配到好对象而接受更多的教育。
①也有研究从父母和家庭的角度定义教育的婚姻回报:在对女性进行教育投资后,女性能够嫁一个更好的丈夫从而能为女方家庭带来更多彩礼。可参见Foster和Rosenzweig(2001)。
如果婚姻市场存在显著的教育性别差异,男性相对受教育水平越高,那么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男性供给的更快增加会引起性别比率失衡,女性受教育的婚姻回报率相对男性会上升。给定男性的受教育水平,能力越强的男性倾向于匹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能给家庭和丈夫带来更多的收益(Benham,1974)。换句话说,教育对女性来说不仅意味着更高教育水平的丈夫,还可能意味着更具经济优势的丈夫。随着男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女性选择受过良好教育水平配偶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而且,受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不断上升②的影响,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必然会随之上升,这进一步提高了女性教育的婚姻回报率。经验研究也发现,高中学历的女性存在着“上嫁”的动机,更愿意增加在婚姻市场上的搜寻等待时间,而城镇女性也愿意在男性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暂时选择推迟结婚年龄而保持单身(邢春冰和聂海峰,2010)。在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竞争中,户籍特征是未婚者在搜寻对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研究把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的婚配定义为“向上婚配”,结果发现非农户籍的男性与农业户籍女性的婚配比重,显著地高于农业户籍男性与非农户籍女性的组合,教育对女性的向上婚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丰龙和何深静,2014)。
②1980年以来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持续高位运行,2000年约为105.62,2010年约为105.48,考虑性别选择性漏报,实际值可能更高(李树茁和果臻,2013)。
综上所述,在婚姻市场上,男性受教育水平相对高于女性且在性别比率上升的条件下,女性受教育具有更高的婚姻回报率。教育对女性向上匹配和实现更高婚姻效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具有更强的教育投资激励。受到经济条件、家长受教育水平、传统观念、女孩出生顺序等因素的影响(彭亚华,2004;李春玲,2009;罗凯和周黎安,2010),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相对不足,导致农村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相对城镇女性处于比较劣势。随着婚姻市场竞争形式的不断变化,实现教育同质婚配或教育向上婚配,成为农村家庭为女孩进行教育投资的动力来源。
三、方法、数据与变量描述(一)识别方法
在我们的分析中,为了匹配到理想的婚姻对象,个人会更有激励投资更多教育,而更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匹配到相应教育层次的对象。因此,我们将本人和配偶的教育程度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构建教育决定模型和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型,组成递归双变量模型:
| $ \begin{array}{l} s_i^ * = z{'_{1i}}{\beta _1} + {\mu _{1i}}\\ y_i^ * = z{'_{2i}}{\beta _2} + \gamma s_i^ * + {\mu _{2i}} \end{array} $ | (1) |
其中,s*i是衡量个体i教育程度的潜变量,y*i是衡量个体i婚姻质量程度的潜变量。z1i和z2i都是外生变量组成的向量组,并且z1i与z2i不完全相同,否则方程(1)中的教育决定方程无法识别。β1、β2、γ为待估计的参数。如果γ=0,我们的模型可称为似无关方程组模型(SUR);如果γ≠0,我们的模型则为递归的联立方程模型;如果γ>0,则意味着教育的婚姻回报显著大于0。首先,我们假设模型的残差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满足外生性条件,即E(z1iμ1)=E(z2iμ2)=0,联合分布为:
| $ \left( \begin{array}{l} {\mu _{i1}}\\ {\mu _{i2}} \end{array} \right) \sim N\left[{\left( \begin{array}{l} 0\\ 0 \end{array} \right),\left( {\begin{array}{*{20}{c}} 1&\rho \\ \rho &1 \end{array}} \right)} \right] $ | (2) |
由于我们未观测到连续型的教育程度指标和婚姻质量指标,参考我们的数据特点,只能选择有序分类变量si和yi分别来衡量教育和婚姻质量,分类变量满足以下条件:
| $ {s_i} = \left\{ \begin{array}{l} 1\;\;\;\;\;\;\;ifs_i^ * \le {m_{11}}\\ 2\;\;\;\;\;\;if{m_{11}} < s_i^ * \le {m_{12}}\\ \vdots \\ K\;\;\;\;\;if{m_{1K - 1}} < s_i^ * \end{array} \right.\;\;\;\;{y_i} = \left\{ \begin{array}{l} 1\;\;\;\;\;\;\;ify_i^ * \le {m_{21}}\\ 2\;\;\;\;\;\;if{m_{21}} < y_i^ * \le {m_{22}}\\ \vdots \\ L\;\;\;\;\;if{m_{2L - 1}} < y_i^ * \end{array} \right.\; $ | (3) |
其中,未知的中断点满足条件:m11<m12<…<m1K-1,m21<m22<…<m2L-1 。线性模型(1)无法进行直接的参数估计,因此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概率模型,转换为标准可估计的probit概率选择模型。代表性个体i在获得教育程度si=k、得到质量为yi=l婚姻的联合概率为:
| $ \begin{array}{l} \Pr \left( {{s_i} = k,{y_i} = l} \right) = \Pr \left( {s_i^ * \le {m_{1k}},y_i^ * \le {m_{2l}}} \right) - \Pr \left( {s_i^ * \le {m_{1k - 1}},y_i^ * \le {m_{2l}}} \right)\\ \;\;\;\;\;\;\;\;\;\;\;\;\;\;\;\;\;\;\;\;\;\;\;\;\;\; - \left[{\Pr \left( {s_i^ * \le {m_{1k}},y_i^ * \le {m_{2l - 1}}} \right) - \Pr \left( {s_i^ * \le {m_{1k - 1}},y_i^ * \le {m_{2l - 1}}} \right)} \right]\\ \;\;\;\;\;\;\;\;\;\;\;\;\;\;\;\;\;\;\;\;\;\;\; = {\Phi _2}\left[{{m_{1k}} - z{'_{1i}}{\beta _1},\left( {{m_{2l}} - \gamma z{'_{1i}}{\beta _1} - z{'_{2i}}{\beta _2}} \right)\theta ,\tilde \rho } \right]\\ \;\;\;\;\;\;\;\;\;\;\;\;\;\;\;\;\;\;\;\;\;\;\;\;\; - \left[{{m_{1k{\rm{ - 1}}}} - z{'_{1i}}{\beta _1},\left( {{m_{2l}} - \gamma z{'_{1i}}{\beta _1} - z{'_{2i}}{\beta _2}} \right)\theta ,\tilde \rho } \right]\\ \;\;\;\;\;\;\;\;\;\;\;\;\;\;\;\;\;\;\;\;\;\;\;\;{\rm{ - }}{\Phi _2}\left[{{m_{1k}} - z{'_{1i}}{\beta _1},\left( {{m_{2l{\rm{ - 1}}}} - \gamma z{'_{1i}}{\beta _1} - z{'_{2i}}{\beta _2}} \right)\theta ,\tilde \rho } \right]\\ \;\;\;\;\;\;\;\;\;\;\;\;\;\;\;\;\;\;\;\;\;\;\;{\rm{ + }}\;\left[{{m_{1k{\rm{ - 1}}}} - z{'_{1i}}{\beta _1},\left( {{m_{2l{\rm{ - 1}}}} - \gamma z{'_{1i}}{\beta _1} - z{'_{2i}}{\beta _2}} \right)\theta ,\tilde \rho } \right] \end{array} $ | (4) |
其中,Φ2表示二元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θ=θ(γ,ρ),${\tilde \rho }$=${\tilde \rho }$(γ,ρ)。我们可以将推导得到的模型(4)称之为联立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simultaneous bivariate ordered probit model),γ≠0时称之为递归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recursive bivariate ordered probit model)。对于有序Probit模型,比较合适的估计方法是最大似然估计。
构建全样本(样本量为N)的对数似然函数:
| $ \ln E = \sum\limits_{i = 1}^N {\sum\limits_{k = 1}^K {\sum\limits_{l = 1}^L {\ln \Pr \left( {{s_i} = k,{y_i} = l} \right)} } } $ | (5) |
由于E(μ1iμ2i)=ρ,如果ρ=0,则意味着E(siμ2i)=0,我们可以直接将模型视作似无关模型,对两个方程分别进行最大似然回归,得到参数γ的无偏估计结果。如果ρ≠0,简单的似无关处理并不能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2SLS、IOP和twostep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都是有偏不一致的,而只有使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FIML),才能得到参数γ和ρ的一致估计(Sajaia,2008)。
(二)变量设定根据数据库所采集的信息,我们的被解释变量为本人受教育程度和配偶受教育程度。在教育决定模型中,我们控制了受访者本人出生时的户口性质、出生时住房类型、民族身份、性别、出生世代、兄弟姐妹数量等,既包含了家庭经济因素,又包含了家庭背景因素,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决定机制。在婚姻决定模型中,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为被解释变量,本人的受教育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初婚时的户口性质、住房性质与住房类型等为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设定如表1所示。
| 变 量 | 设 定 | |
| 本人受教育程度 | s | 未上学设置为0,小学为1,初中为2,高中阶段(高中、中专、职高技校)为3,大学专科为4,大学本科为5,研究生及以上为6 |
| 配偶受教育程度 | y0 | 未上学设置为0,小学为1,初中为2,高中阶段(高中、中专、职高技校)为3,大学专科为4,大学本科为5,研究生及以上为6 |
| 当地配偶平均受教育程度 | z08 | 当地样本中配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
| 配偶相对受教育程度 | y1 | 配偶受教育程度高于或等于当地配偶平均受教育水平,则为1;否则为0 |
| 出生时居住地类型 | z01 | 城区和镇为1,其他为0 |
| 出生时户口性质 | z02 | 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之前为非农业户口)为1; 其余为0 |
| 出生时住房类型 | z03 | 农村住宅(砖石或钢混结构房屋),楼房单间、筒子楼,平房为1;别墅、联排别墅,成套单元楼房为2;其余为0 |
| 民族身份 | z04 | 汉族为0,少数民族为1 |
| 性别 | z05 | 女性为1,男性为0 |
| 出生世代 | z06 | 60岁及以上的人口设定为0(按2011年推算,其出生年份恰好为1950年代之前,简称“50前”),50-59岁设定为1(“50后”),40-49岁人口设定为2(“60后”),30(含30)-39岁设定为3(“70后”),30岁以下设定为4(“80后”) |
| 兄弟姐妹数量 | z07 | 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姐妹数量(包括16周岁后去世的) |
| 初婚时户口性质 | z22 | 非农业户口,或居民户口(之前是非农业户口)为1;农业户口 |
| 初婚时所住房屋类型 | z23 | 成套单元楼房、别墅或连排别墅设置为2,农村住宅(砖石或钢混合结构房屋)、楼房单间、筒子楼、平房为1,其他设置为0(包括农村住宅、棚户、简易住房) |
| 初婚时所住房屋性质 | z25 | 家庭自建自购住房为2 ,租/借公房或他人住房为1,其他为0 |
我们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①。该调查以家庭为单位,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展开调查访问。每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样本量约7000-8000个家庭。先后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开展了三期调查。2011年的调查涉及全国25个省份以及5个城市的市区,调查范围涉及472个村、居委会(SSU),以每个SSU的地图地址为抽样框作为实地抽样的基准,从中抽取对应的家庭户或集体户,2011年调查了7552个家庭。
①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培林。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2011年数据总计7036个样本为有效样本,其中未婚样本631个,初婚有配偶样本5478个,再婚有配偶样本173个,离婚样本153个,丧偶样本574个,同居样本24个,不清楚的样本3个。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首先删掉未婚样本和不清楚的样本,再删去教育程度缺失和不清楚的样本,实际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 5536个。
首先,我们描述了本人与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见表2。
| 单位:人,%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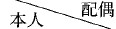 | 未上学 | 小学 | 初中 | 高中阶段 | 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 研究生 | 合计 | 占比 |
| 未上学 | 244 | 193 | 130 | 38 | 3 | 0 | 0 | 608 | 10.98 |
| 小学 | 218 | 703 | 418 | 100 | 8 | 3 | 1 | 1451 | 26.21 |
| 初中 | 102 | 357 | 960 | 267 | 51 | 16 | 0 | 1753 | 31.67 |
| 高中阶段 | 29 | 81 | 292 | 430 | 104 | 46 | 2 | 984 | 17.77 |
| 大学专科 | 2 | 18 | 55 | 120 | 142 | 62 | 4 | 403 | 7.28 |
| 大学本科 | 1 | 1 | 16 | 49 | 65 | 157 | 15 | 304 | 5.49 |
| 研究生 | 0 | 0 | 1 | 3 | 2 | 12 | 15 | 33 | 0.6 |
| 合计 | 596 | 1 353 | 1 872 | 1 007 | 375 | 296 | 37 | 5 536 | 100 |
| 占比 | 10.77 | 24.44 | 33.81 | 18.19 | 6.77 | 5.35 | 0.67 | 100 | — |
总体而言,本人与配偶受教育程度最为接近,各教育阶段约一半人的配偶受教育程度与本人相同,这也符合我们前文的分析。由于我们使用的样本是进入婚姻年龄段的样本,样本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比例基本符合我国教育发展阶段。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2013年达到34.5%①;样本中接受大学及以上(专科、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个体大约为13%(本人为12.79%,配偶为13.37%)。表2中显著的特征事实是,本人与配偶的匹配模式在教育维度上更多地体现为正匹配,也就是说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与本人受教育程度正相关,未上学人员在婚姻市场上更多地匹配到未上学人员,大学及以上人员更多地匹配到大学及以上人员。
①数据来源:教育部《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为了更好地观察样本,我们对变量进行了分性别统计,见表3。
| 变量 | 男 | 女 | ||||||
| 样本量(个) | 最小值 | 中位数 | 最大值 | 样本量(个) | 最小值 | 中位数 | 最大值 | |
| 注:由于兄弟姐妹数量(z07)实际有效样本只有5521个,因此后文回归的最大样本为5521个。 | ||||||||
| y1 | 2607 | 0 | 0 | 1 | 2929 | 0 | 1 | 1 |
| z02 | 2607 | 0 | 0 | 1 | 2929 | 0 | 0 | 1 |
| z03 | 2607 | 0 | 0 | 2 | 2929 | 0 | 0 | 2 |
| z04 | 2607 | 0 | 0 | 1 | 2929 | 0 | 0 | 1 |
| z06 | 2607 | 0 | 2 | 4 | 2929 | 0 | 2 | 4 |
| z07 | 2604 | 0 | 3 | 12 | 2917 | 0 | 3 | 11 |
| z22 | 2607 | 0 | 0 | 1 | 2929 | 0 | 0 | 1 |
| z23 | 2607 | 0 | 1 | 2 | 2929 | 0 | 1 | 2 |
| z25 | 2607 | 0 | 2 | 2 | 2929 | 0 | 2 | 2 |
从表3中可以看到,女性样本为2929个,占52.91%;男性样本为2607个,占47.09%。这似乎与我国性别结构失衡的现状有出入,实则不然。人口统计表明,我国新生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非常严重,而我们所使用的样本基本排除了青年未婚人口。实际上,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男性人口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至与女性相等甚至低于女性比例的状态,部分原因是女性的预期寿命要高于男性。而出生世代的中位数为2,代表40-50岁人群(“70后”),反映出我国的性别结构失衡问题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凸显出来的。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家庭兄弟姐妹个数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位数是3,最大值超过了10,这些例外值都出现在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口样本里。
四、实证结果分析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的计量过程需要分为三个步骤来进行。首先,我们需要检验性别身份对教育获得的边际作用,识别出女性身份的不利影响及其机制;其次,我们需要检验教育与婚配模式的关联机制,估计得到教育的婚姻回报率,并识别出女性身份对婚配结构的积极影响;第三,我们需要检验女性身份对教育获得影响机制的逆转,需要检验性别身份的教育效应,教育与婚配模式的关联机制,并分析不同出生世代人群所存在的效应差异。
(一)教育的决定因素及其性别差异首先,我们需要识别个体教育成就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再进行性别之间的对比。利用全部样本进行的probit回归结果,报告在表4中。
 |
本人受教育程度 | |||
| (1) | (2) | (3) | (4) | |
| 注:括号里报告的是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水平上显著;出生世代_50s、_60s、_70s、_80s分别表示出生在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 | ||||
| 出生时住房类型 | 0.691 ***(0.026) | 0.286 ***(0.030) | 0.279 ***(0.030) | 0.337 ***(0.030) |
| 性别 | -0.385 ***(0.028) | -0.476 ***(0.029) | -1.029 ***(0.051) | |
| 兄弟姐妹数量 | -0.098 ***(0.007) | -0.050 ***(0.008) | 0.012(0.009) | -0.074 ***(0.008) |
| 性别×兄弟姐妹数量 | -0.126 ***(0.008) | |||
| 出生时户口性质 | 1.026 ***(0.041) | 1.023 ***(0.040) | 0.932 ***(0.040) | |
| 民族身份 | -0.221 ***(0.051) | -0.213 ***(0.051) | -0.200 ***(0.051) | |
| 出生世代 | 0.291 ***(0.013) | 0.287 ***(0.013) | ||
| 性别×出生世代_50s | 0.335 ***(0.063) | |||
| 性别×出生世代_60s | 0.756 ***(0.059) | |||
| 性别×出生世代_70s | 1.089 ***(0.064) | |||
| 性别×出生世代_80s | 1.114 ***(0.080) | |||
| N | 5521 | 5521 | 5521 | 5521 |
| pseudoR 2 | 0.065 | 0.117 | 0.118 | 0.109 |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否控制兄弟姐妹数量、出生时户口性质、民族身份与出生世代等变量的影响,女性身份的教育效应显著为负。也就是说,排除了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平均意义上女性受教育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对比表4中列(2)和列(3)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性别身份的负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女性在家庭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越大,因此来自多子女家庭的女性,接受教育的弱势地位更趋强化。由此也可以推测,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女性,其女性身份的不利影响相对最弱。结合列(2)、列(3)和列(4),我们进一步分解性别身份效应的世代差异,结果发现越晚出生的女性,平均意义上能够达到更高的教育成就。表4的结果还显示,家庭住房类型、城镇户籍等变量对教育获得的作用显著为正,家庭兄弟姐妹数量、少数民族身份显著为负,表明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依然是决定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
(二)教育的婚姻回报及其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我们已经在表4中初步识别了教育的决定因素,并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出生世代差异,接下来我们进行分样本的递归双变量Probit回归。使用递归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首先需要检验误差的相关系数是否为0。如果相关系数显著不为0,表明存在相关性和内生性,传统的最大似然估计(ML)结果有偏,而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是一致有效估计。因此,我们首先用最大似然估计我们的联立模型,并检验相关系数相关性的原假设:ρ=0。FIML回归结果与LR检验值一并报告在表5中。
| (1) | (2) | (3) | (4) | (5) | |
| 全样本 | 50s | 60s | 70s | 80s+ | |
| 注:括号里报告的是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水平上显著;每一列表示对双变量Probit模型方程组的一次全样本FIML估计结果。 | |||||
| 被解释变量:本人受教育程度 | |||||
| 出生时住房类型 | 0.286 *** (0.030) | 0.187 *** (0.063) | 0.175 *** (0.058) | 0.519 *** (0.063) | 0.487 *** (0.098) |
| 兄弟姐妹数量 | -0.050 *** (0.008) | -0.036 ** (0.015) | -0.079 *** (0.015) | -0.158 *** (0.020) | -0.201 *** (0.043) |
| 性别 | -0.501 *** (0.029) | -0.648 *** (0.061) | -0.382 *** (0.056) | -0.342 *** (0.064) | -0.262 ** (0.109) |
| 民族 | -0.212 *** (0.051) | -0.275 *** (0.104) | -0.214 ** (0.093) | -0.224 ** (0.113) | -0.126 (0.181) |
| 出生时户口性质 | 1.016 *** (0.041) | 1.015 *** (0.083) | 1.061 *** (0.081) | 0.776 *** (0.094) | 0.780 *** (0.166) |
| 出生世代 | 0.290 *** (0.013) | ||||
| 被解释变量:配偶受教育程度 | |||||
| 本人受教育程度 | 1.401 *** (0.100) | 1.737 *** (0.291) | 0.999 *** (0.176) | 1.183 *** (0.184) | 1.392 *** (0.399) |
| 性别身份×本人受教育程度 | 0.195 *** (0.014) | 0.136 *** (0.041) | 0.234 *** (0.026) | 0.121 *** (0.024) | 0.010 (0.039) |
| 初婚时住房类型 | 0.274 *** (0.028) | 0.256 *** (0.062) | 0.210 *** (0.052) | 0.320 *** (0.062) | 0.313 *** (0.096) |
| 初婚时户口性质 | 0.607 *** (0.051) | 1.052 *** (0.119) | 0.667 *** (0.112) | 0.560 *** (0.099) | 0.022 (0.166) |
| 初婚时住房性质 | -0.153 *** (0.031) | -0.159 ** (0.067) | -0.068 (0.062) | -0.047 (0.072) | -0.050 (0.119) |
| 出生世代 | 0.203 *** (0.018) | ||||
| γ | -1.002 *** (0.102) | -1.723 *** (0.292) | -0.488 *** (0.180) | -0.480 ** (0.193) | -0.315 (0.382) |
| ρ | -0.001 | 0.254 | -0.070 | -0.007 | -0.155 |
| LR检验值 | 88.92 *** | 26.08 *** | 8.61 *** | 5.98 ** | 1.33 |
| N | 5521 | 1193 | 1501 | 1124 | 436 |
表5给出了双变量Probit模型方程组的联合估计结果,由于我们的双变量模型的第二个结构方程存在一定的内生性,简单的ML估计得到的结果将是有偏的(低估),FIML才能得到一致有效估计,而FIML估计也是得到γ一致估计的唯一方法。基本的结果总结如下:
首先,教育的婚姻回报显著为正,存在着较强的依教育而正匹配的婚姻配对模式,这与李煜(2008)对50年以来我国婚姻的教育匹配趋势一致。表5显示,即使控制了初婚时的经济条件,不论是出生在1950年代还是出生在1980年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匹配到高受教育程度配偶的概率越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希望“嫁得好”或“娶得好”(与一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对象结婚),那么提高本人的受教育程度是一条增加成功概率的有效路径。
其次,女性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机会与男性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劣势,但女性在匹配一名更高受教育程度配偶的可能性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女性受教育的婚姻回报高于男性。反映在表5的回归结果中,就是教育决定模型中女性身份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婚配模型中性别身份与教育的交叉项显著为正。女性在受教育过程中因性别而面临的如前文所述的不利境地,并不会出现在婚姻匹配中。
第三,1950年代出生的群体,其教育的婚姻回报率最高,这与这代人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有密切联系。受过良好教育水平的婚配对象供给越少,匹配概率相对越低,教育的婚姻回报则越高。越早世代出生的女性,受到性别身份等因素的不利影响更多,平均受教育程度更低。表4中列(4)的回归结果已经初步显示了这一点,而表5不同出生世代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区分了差异。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1977年恢复高考,1960年代及其以后世代出生的人口正好能够享受政策红利,而部分50后群体也能够赶上末班车,因此1960年代及以后年龄群体的受教育机会更多,从而教育的婚姻回报相对降低;其次,随着1986年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改善了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机会,女性也从公共教育事业发展中获益良多,但1950年代出生的女性基本难以享受到义务教育制度带来的福利;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家庭收入不断提升,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社会文化中的男孩偏好与性别歧视逐渐淡化,性别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越晚出生世代的人群能够享受更多的教育机会,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表5中列(1)出生世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这一点。
综合以上分析,如果女性为了提高其婚配质量,找到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那么女性就需要更好地提升本人的受教育程度。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更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好的社会地位。这样一来,婚姻就为女性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增加了新的动力来源。同理,男性也能通过教育而匹配到更好的女性对象。但是同等条件下,女性匹配到高学历男性的概率要高于男性匹配到高学历女性的概率,而受教育过程则刚好相反。因此,随着婚姻中双向选择障碍的逐渐消除(自由恋爱),婚姻市场的竞争信号可能会逆向传递到教育决策过程中,激励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
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资源与社会福利分配体制,婚配模式也随之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放松户籍限制,跨户籍通婚(主要体现为城镇男性与农村女性之间)随之显著增加(邢春冰和聂海峰,2010)。预计城乡之间的男性与女性在教育与婚配结构中,存在程度各异的教育与婚配激励。因此,有必要区分城乡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因此,我们选择了婚姻状态为“初婚有配偶”的样本,并区分出生时户口性质为城镇和农村的样本,以及区分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中。
| (1) 城镇、女性 | (2) 城镇、男性 | (3) 农村、女性 | (4) 农村、男性 | |
| 注:括号里报告的是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信心水平上显著;本表所有模型都是使用FIML估计所得;每一列表示对双变量Probit模型方程组的一次全样本估计结果。 | ||||
| 被解释变量:本人受教育程度 | ||||
| 出生时住房类型 | 0.248 ***(0.070) | 0.124(0.077) | 0.391 ***(0.051) | 0.255 ***(0.056) |
| 兄弟姐妹数量 | -0.074 ***(0.023) | -0.031 *(0.019) | -0.068 ***(0.013) | -0.031 ***(0.012) |
| 民族 | -0.016(0.167) | -0.176(0.153) | -0.295 ***(0.081) | -0.207 ***(0.078) |
| 出生世代 | 0.328 ***(0.039) | 0.223 ***(0.039) | 0.343 ***(0.020) | 0.256 ***(0.020) |
| 被解释变量:配偶受教育程度 | ||||
| 本人受教育程度 | 1.669 ***(0.631) | 0.947 **(0.445) | 1.504 ***(0.187) | 0.561 ***(0.135) |
| 初婚时住房类型 | 0.269 ***(0.076) | 0.129(0.085) | 0.177 ***(0.048) | 0.299 ***(0.046) |
| 初婚时户口性质 | 0.334(0.278) | 0.078(0.210) | 0.399 ***(0.085) | 0.500 ***(0.082) |
| 初婚时住房性质 | -0.012(0.073) | -0.153 **(0.070) | -0.102 *(0.059) | -0.182 ***(0.053) |
| 出生世代 | 0.012(0.096) | 0.086(0.152) | 0.055(0.047) | 0.376 ***(0.041) |
| γ | -1.104(0.704) | 0.164(0.582) | -0.791 ***(0.205) | -0.184(0.224) |
| ρ | 0.116 | -0.723 | -0.094 | 0.227 |
| LR检验值 | 1.54 | 2.10 | 16.59 | 0.14 |
| N | 673 | 646 | 2244 | 1958 |
表6所报告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前文的分析。尤其是婚配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系数回归结果非常显著,其教育的婚姻回报显著高于农村男性;类似地,城镇女性教育的婚姻回报也高于城镇男性。对于农村女孩而言,通过教育—婚配途径改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是一条可行性非常强的路径。我们可以对比表6中男性样本与女性样本的回归结果,来分析农村女性受教育和婚配情况。对比表6中的列(3)和列(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虽然家庭兄弟姐妹数量与少数民族身份对农村女性受教育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男性,但家庭经济条件和出生世代对女性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男性。随着教育普及与普惠性教育资源的增加,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使得农村女性受益相对更多,这与叶华和吴晓刚(2011)的研究一致。类似地,婚配模型回归结果也显示,同等条件下,农村女性匹配到一个既定教育程度男性配偶的概率要高于农村男性匹配到同等教育成就的女性。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就是婚姻市场上对教育特征竞争的概率逆转,即男性匹配到高教育水平女性的难度要大于女性匹配到同样教育水平的男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如果要匹配到一位更理想的婚姻对象,更有激励提高自身的教育程度。当然,由于城镇户籍地位对教育婚配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要弱于城镇女性,从婚姻匹配模型教育边际作用的对比中可以发现这一点。
与此同时,为了检验婚配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改变婚配模型被解释变量,以配偶相对受教育水平来表示,得到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分析保持高度一致,篇幅所限,不再报告结果。
(三)性别身份效应的逆转:未婚样本的再回归上文我们已经使用了具有类似婚姻经历的样本,实证发现教育能够在婚配过程中带来的好处,以此论证教育的决定机制。要使这一结论更可靠,必须要用证据来说明未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同样受到婚配过程与模式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将进一步利用“80后”未婚样本,对教育决定模型进行再回归。由于没有婚配模型,我们将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即配偶平均受教育水平,回归的结果报告在表7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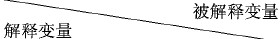 |
(1) 本人受教育程度 | (2) 本人受教育程度 |
| 注:括号里报告的是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水平上显著。 | ||
| 出生时住房类型 | 0.309 ***(0.075) | 0.196 **(0.083) |
| 兄弟姐妹数量 | -0.191 ***(0.047) | -0.162 ***(0.050) |
| 民族身份 | 0.351 **(0.175) | 0.355 **(0.175) |
| 当地配偶平均受教育程度 | 0.513 ***(0.082) | 0.512 ***(0.083) |
| 性别 | 0.194 **(0.095) | |
| 出生时户口性质 | 0.385 ***(0.120) | |
| 女性×城镇户籍 | 0.350 **(0.162) | |
| 男性×农村户籍 | -0.218 *(0.120) | |
| 男性×城镇户籍 | 0.195(0.147) | |
| pseudo R 2 | 0.087 | 0.087 |
| N | 526 | 526 |
表7所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因素的回归系数与之前保持一致;性别身份的回归系数由之前的显著为正转为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里,男性身份不再有利于个体获得更多教育,同等条件下女性获得更高教育成就的概率更高。结合性别身份与户籍身份的交叉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一点。表7中第(1)列报告了性别身份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户籍身份的系数显著为正。第(2)列在保持其他变量固定的前提下,引入性别身份和户籍身份的交叉项解释了第(1)列中的回归结果。由于对照组是农村女性,可以发现:农村男性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在获取既定教育成就方面,农村男性不仅没有超过农村女性,反而低于农村女性,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的男女性别差异不断缩小;城镇女性的系数显著为正,城镇女性相对于农村女性具有显著优势;城镇男性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城镇男性的优势不明显。因此,城镇户籍身份带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村男性与城镇男性之间,以及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之间;而女性身份带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城镇女性相对农村男性的优势更大。
此外,少数民族身份的回归系数由负转正,这与我国近年来不断出台少数民族教育倾斜政策分不开。由于我们使用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个体样本,而有研究发现,少数民族近年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量要超过汉族(孙百才等,2014),因此民族身份有利于促进新时期少数民族群体获得更多教育。引入已婚样本报告的配偶受教育程度平均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进一步佐证了我们前文的分析结果,为了匹配到教育程度更高的婚姻对象,个体有动力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根据表7的系数回归结果,我们进行边际效应转换(margins),计算了平均状态下分性别、分城乡群体的达到不同教育成就的概率,报告在表8中。
| 农村女性 | 农村男性 | 城镇女性 | 城镇男性 | |
| 高中阶段 | 0.379 | 0.397 | 0.322 | 0.351 |
| 大学专科 | 0.229 | 0.201 | 0.257 | 0.248 |
| 大学本科 | 0.193 | 0.140 | 0.298 | 0.249 |
| 研究生 | 0.003 | 0.002 | 0.009 | 0.005 |
表8清晰地显示了80后群体受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首先,农村男性仅完成高中阶段教育的概率最高;其次,城镇女性完成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概率最高;第三,农村女性完成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概率要高于农村男性,这意味着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女性受教育面临的不利境地已经初步得到了扭转。一份利用CGSS(2008)数据的经验研究同样发现,虽然男孩上大学的机会相对女孩更高,但是扩招之后男性的优势在下降,而农村地区下降的幅度更大,农村地区的女性得到了更多新增教育机会,改善了教育劣势地位(张兆曙和陈奇,2013)。
虽然农村内部的性别差异趋于消失,但是城乡之间的鸿沟依然没有消除。农村人口虽然已相当于城市人口,但农村人口中的大学专科及以上层次教育机会都更少。这一点,我们从精英高校的典型——北京大学的案例分析中便可窥见一斑。1978年北大招收女生的比例为20.1%,2005年上升到46.2%,近年来总体上维持在40%以上,其中来自农村的男生人数约为10%,而来自农村的女生人数则不足5%(刘云杉和王志明,2008)。这说明女性受教育机会改善的同时,城乡女性的受教育差异却没有缩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近年来,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迅速改善。从以往的研究结果看,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家庭教育投资存在着显著的“男性偏向”,农村女孩受教育机会受到负面影响。即使是计划生育减少了家庭子女的数量,但这并不构成足够支持农村家庭对女孩进行更多教育投资的理由。早期研究发现,女性身份不利于获得更多教育,性别之间的教育差异被逐渐拉大。然而,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得到如此迅速的改观?
本文利用CSS 2011年微观数据,构建教育和婚配的双有序变量递归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教育获得的决定因素以及教育的婚姻回报。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结果显示,婚姻市场存在显著为正的教育回报率,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匹配到高教育水平对象的概率也越高;就性别优势而言,男性身份有助于获得更多教育,但不利于匹配到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对象。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女性教育回报率相对男性更高,农村女性的教育回报相对城镇男性的教育回报更高,教育的边际效果也更强。最后,未婚样本的教育决定回归结果显示,当地已婚样本配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激励了未婚者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
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不仅可以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回报,如生育行为优化、健康提升和后代更好地成长等,因此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是加快社会进步的理想选择(庄平,1996)。那么,如何改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本文提供了这样一个政策思路,即生育女孩的家庭为了让女孩嫁得更好,而具有较强的教育投资愿望。但是,家庭的教育投资愿望可能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从而无法达到预想的教育目标。因此,为在校女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财务资助,降低家庭经济条件对女性受教育的负面影响,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另外,实现平等自由的婚配,也是保障教育的婚姻回报为正的重要前提。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女孩的婚姻依然受到较多家庭和社会习俗因素的干扰,这也会妨碍婚姻对女性受教育的激励作用。
| [1] | 柯丽香,陈建新,伍芷蕾.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教育不均等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3). |
| [2] | 李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1):14-18. |
| [3] | 李树茁,果臻.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演变[J].中国人口科学,2013,(2). |
| [4] | 李煜.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J].中国人口科学,2008,(3). |
| [5] | 刘云杉,王志明.女性进入精英集体:有限的进步[J].高等教育研究,2008,(2). |
| [6] | 罗凯,周黎安.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一个基于家庭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经济科学,2010,(3). |
| [7] | 牛建林,齐亚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对男女教育均衡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0,(S1). |
| [8] | 彭亚华.少数民族女童低学业成就的归因分析与对策[J].民族教育研究,2004,(1). |
| [9] | 孙百才,张洋,刘云鹏.中国各民族人口的教育成就与教育公平——基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比较[J].民族研究,2014,(3). |
| [10] | 王丰龙,何深静.中国劳动力婚姻匹配与婚姻迁移的空间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4,(3). |
| [11] | 卫倩平.基于性别差异的教育公平[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32). |
| [12] | 邢春冰,聂海峰.城里小伙儿遇到农村姑娘:婴儿户口、户籍改革与跨户籍通婚[J].世界经济文汇,2010,(4). |
| [13] | 叶华,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J].社会学研究,2011,(5). |
| [14] | 张兆曙,陈奇.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2). |
| [15] | 庄平.论女性教育的社会回报[J].社会学研究,1996,(2). |
| [16] | Abramitzky R., Delavande A., Vasconcelos L. Marrying Up: The Role of Sex Ratio in Assortative Match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1,3(3):124-157. |
| [17] | Barro R. J., Lee J.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4: 184-198. |
| [18] | 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Ⅰ[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81(4):813-846. |
| [19] | Benham L. Benefits of Women's Education within Marria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82(2):S57-S71. |
| [20] | Ben-Porath Y., Welch F. Do Sex Preferences Really Matter?[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6, 90(2):285-307. |
| [21] | Butcher K. F.,Case A. The Effect of Sibling Sex Composition on Women's Education and Earning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 531-563. |
| [22] | Burdett K., Coles M.G. Marriage and Clas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12(1):141-168. |
| [23] | Eugene C., Aloysius S. Who Marries Whom and W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114(1):175-201. |
| [24] | Foster A., Rosenzweig M. Missing Women,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EB/O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vailable at http://adfdell. pstc. brown. edu/papers/sex. pdf, 2001. |
| [25] | Kalmijn M. Intermarriage and Homogamy: Causes, Patterns, Trend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24:395-421. |
| [26] | Mare R. D. Five Decades of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56(1):15-32. |
| [27] | McPherson M., Smith-Lovin L., Cook J.M.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27:415-444. |
| [28] | Oreopoulos P., Salvanes K.G. Priceless: The Nonpecuniary Benefits of Schooling[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1,25(1):159-184. |
| [29] | Psacharopoulos G., Patrinos H.A.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 Further Update[J]. Education Economics, 2004, 12(2):111-134. |
| [30] | Schwartz C.R., Mare R.D.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from 1940 to 2003[J]. Demography, 2005,42(4):621-646. |
 2015, Vol. 17
2015, Vol. 17


